「漫步」羅府
在南加住了这么久,很少有机会能在这「天使之城」的市中心散散步。下午三点钟,正是LA最美好的时候——阳光不遗余力地给人注入活力,像是把人带入了一个高饱和度的世界。按理来说,这种午后的休闲,应该很是惬意。
但是,我只感受到了一股股的悲凉。
光照的映衬下,本应生机勃勃,有着烟火气的街道,变得阴沉沉的。小东京里的购物广场,地下室的“小秋叶原”,店铺一个个漆黑一团,为数不多开着的几家店,也门可罗雀。这个地方,我第一次来洛杉矶的时候曾经造访过。永远找不到的停车位,摩肩接踵的人潮,和热闹的小铺子们。现在?阴暗的地下通道里,唯一开着的,是空无一人,但是亮堂堂的扭蛋机广场,和对着空邃的走道,机械般放着开朗活泼声音的大头照机。

小东京的广场里,游客们聚集在网红店,「出片」背景附近,享受着阳光,而在一旁,几个无家可归者推着自己的「交通工具」——从超市顺出来的购物车,在大街上漫步。人行横道边上,小贩在路边上卖着那些本应该在「thrift store」见到的伴手礼,配着边上卖艺的人的,从大喇叭传出来的二胡声。

热闹吗?可能还可以。不过出了游客聚集的两个广场,街上遍布倒闭的门脸,仿佛诉说着一段段回忆。终于「开放堂食」的韩国炸鸡店,本应明亮的玻璃上,是一层又一层的涂鸦。广场里别的商铺,里面挂着2023年活动的海报,大门紧锁。「艺术区」的大楼倒是有一些艺术,不过不在里边,在周围的墙上。

阳光的边界
LA变了吗?变了,也没变。一日复一日,南加特有的,火热而明亮的阳光打在这片土地上,照亮着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的心。但是,我所听到、看到、感受到的一切都在告诉我:人们心中的阴霾,越来越难以被这温暖的阳光所治愈了。
离游客区越远,从小东京走到LA市中心的路上,这份失落和悲伤便变得愈发明显。街边的「简易房」们喋喋不休地讲着「居民」们的故事,而更有人在路边躺着,用力吸收着太阳的温暖。

我稍微冒了下险——去贴着边角,看了看天使之城失落的那个边隅:Skid Row。这里倒是挺有烟火气的,不过我宁可希望没有。大街上的人们,在楼房废墟的阴影下,享受着精神物质带来的刺激;路口旁偷偷交头接耳的两个人,像是在兜售什么东西;而墙上的海报与涂鸦,则在宣扬一些更可怕的东西……

求生的本能驱使我快速离开了那里,我不想让今天变成我人生的最后一天。但是,这些也共同地组成了这个帝国挽歌的一部分。有人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什么吗?有人能感知到它的衰落,崩溃,和正在散发出的恐怖主义吗?有,至少在象牙塔里,在这自由之城,天使之城的大街上,人们都好像在议论纷纷,抗议的声音此起彼伏,但是这好像也并不能改变什么。每天的新闻越来越抽象,对少数族裔、边缘群体的攻击一天比一天致命。而到最后,真的有人在意吗?好像也没有。

丛林社会,和「赢学」
我一直觉得美国是一个巨大的丛林社会,胜者为王,败者为寇。从历史上看,美国创建的这短短几百年中,几乎一直是在以占领、扩张、和掠夺维系的。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的,对北美原住民的侵略和恩将仇报,到为了石油进行的掠夺,再到金融场上的一次次「割韭菜」,这个地方一直在吸引着有这样想法的,希望自己也能通过扩张,发展,和掠夺,分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杯羹的人。但是现在,所有的消息都在告诉我们,现在的世界没有那么多资源去掠夺了。结果就是,这个帝国开始了它的崩塌。
而这个靠着「赢」别人起家的地方的人们,会相信吗?会相信自己现在没有办法去「赢」别人吗?必然不会。所以会有那么多的,我觉得难以置信的声音,将一个纳粹头子选上来,为了给自己发声,为了能让这个集体意志去找一些群体,放上祭台,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做他们的「赢学」美梦了。

从某些方面来看,这样的发展,是个必然。但不幸的是,现在首先被放在祭台上的,是移民和跨性别群体,而跨性别移民则首当其冲。很多在美国的人,看到现在的美国,会当那个「理中客」,觉得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之后,这个地方肯定会拨乱反正的。而拨乱反正都需要一些代价。不幸的是,我们,成为了那个代价。
对立,真的是对立吗?
从另一方面来看移民这件事,我曾经一度觉得,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对于移民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:一方全力支持,一方全面反对。而现在来看,我觉得这两派人对于移民这个群体的看法,是一致的。他们在从不同方向上,平等且根本性地歧视移民群体。对于这里的左派来说,移民群体等于那些可怜的,弱小的,需要救济的人。让他们来,可以很好地占领道德高地,满足这些人的成就感。而对右派来说,移民群体是可憎的,不学无术的人,来抢工作、蹭福利。把他们打死,自己的饭碗,福利就能保住了。而真实的移民群体的样子,就被湮没在了这些人的对立、吵闹、和宏大叙事之中。无人在意,也无人得知。
而这背后所体现出的,在对立面上的一致性和「赢学」,不只在移民这一个地方上。所谓的男权和一些激女(radfem)的性别斗争,本质上也是在一个一致,自洽的空间进行的。男权说世界必须男尊女卑,而一些人会去说世界必须女尊男卑。看起来他们针锋相对,而他们在核心问题上是很一致的——性别问题上,总得有一个尊,一个卑。总得有一方「赢」过另一方。而真的必须要这样吗?我们在反对男权的时候,真的需要创造出一个完全一致,甚至有些同步的,男权的对立面出来吗?
女权和「性别范式」
在小东京的紀伊國屋书店里,我偶然看到了上野千鹤子的「厌女」一书。很久没有在书店里捧着一本书,慢慢地读完了。很多书中所描绘的现实问题振聋发聩,她也谈到了很多女性在现实生活中,尤其是在性方面,和婚恋关系上遇到的种种问题。但是通篇读下来,我的感受是:这本书,或者上野千鹤子本人的女权论调,是建立在由男权所构建的所谓「性别范式」上的。
这本书从最开始,就在默认女性本身,是弱势的那一方。在性能力上,在社会上,在婚恋市场上等等。所以需要搞女权,所以需要让女性「变强」,所以要向上爬,去和更上层的男性结为伴侣。而对于不在性别二元论体系下的人们,她认为,这些人,尤其是跨性别女性倾向者(transfem),都是因为「不够格当男人,从而被男性群体排除开外的存在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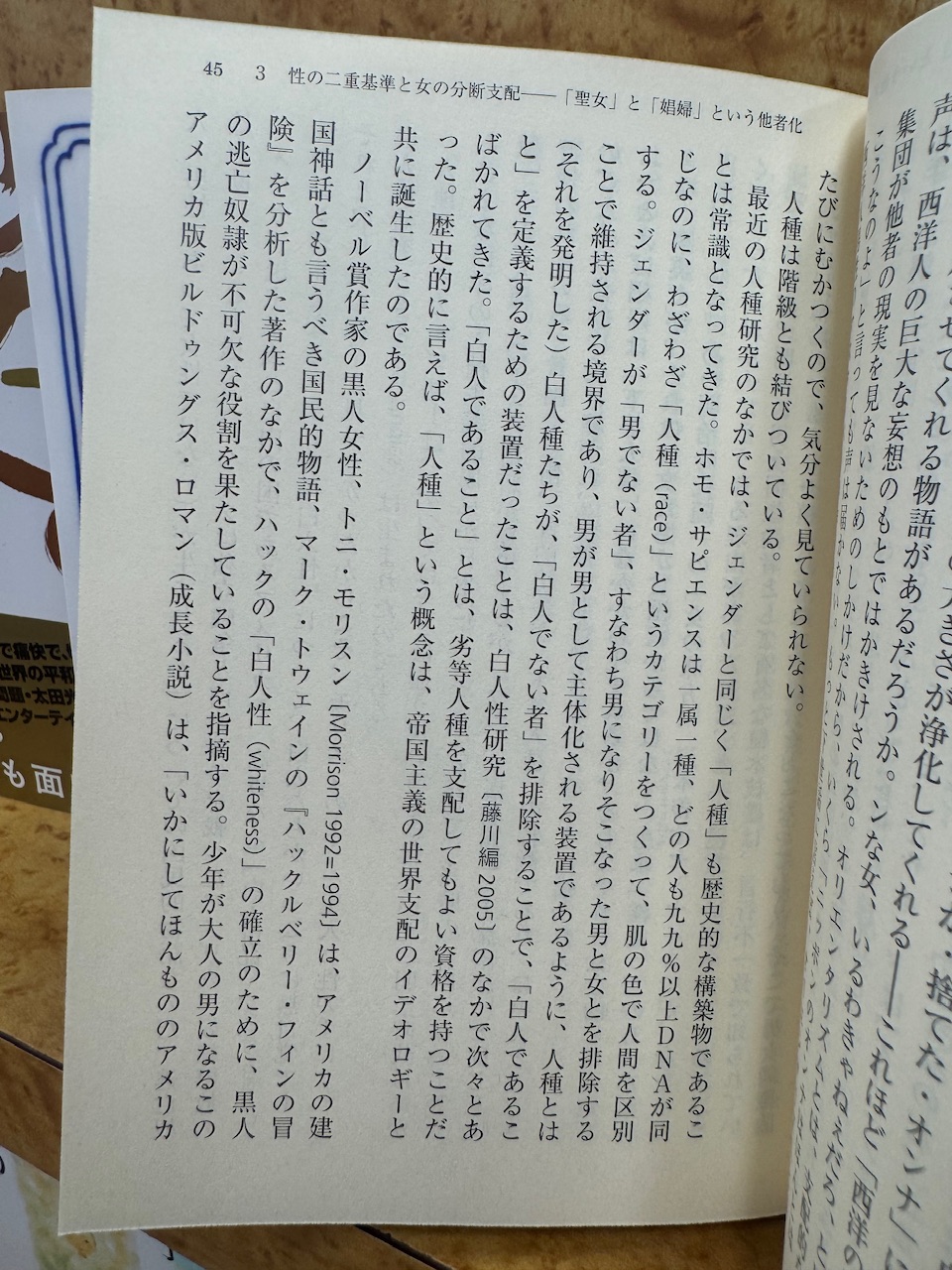
先不谈这本书对于不同性取向者的无视,和对跨性别,以及性别酷儿的无知,这本书所散发出的信息就是,女性本弱,或者说女性在很多方面不如男性。而这一点,恰好是男权社会所构建的性别范式之一。我能理解为什么上野千鹤子会这么想。作为一个20世纪中期出生的人,她对于性别的思考,对于社会问题的研究已经在她所在的年龄段里很通透了。但我不能理解的是,很多所谓「排跨激女」,把这位即将耳顺之年的人的想法当成圣经和进步的法宝,而不想想,为什么一个十几二十的人,要追求和一个76岁的人,在社会议题上想法同步呢?如果在追求进步的道路上,我们都想不断提高自己,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话,我们何不从自己出发,与别人交流,从而形成自己的思考,并推动自己之后继续的进步呢?
时代要发展,版本要更迭,而其中最重要的不是把谁的想法当成珍宝,而是要从中孕育出自己的精神,那道能支撑自己,走过这段跌宕起伏人生的光。